你的購物車是空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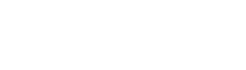


拜訪真真 鑲嵌玻璃研究所的這天,我們來到他位在士林的老屋二樓工作室,挑高的天花板上,掛著各式各樣的鑲嵌玻璃吊燈,幽微的燈光透過玻璃照射,變得有些朦朧,宛如黑夜裡的點點繁星,令人忍不住屏息凝視。仔細觀看會發現,裡頭有些吊燈是由傳統老窗花玻璃所製作,這些看似平凡常見的玻璃,在真真主理人張博傑的巧手之下,成了新舊融合的藝術品。




從新媒體藝術到傳統工藝創作
博傑說,自己從小喜歡畫畫,也覺得創作是件很好玩的事,但若只是做純繪畫,創作的發展還是有些狹窄,為了跳脫畫畫以外的方式,便選擇讀了實踐建築系,在這裡,建築不只是建築,還有更多的可能性。當時在做建築研究時,常常需從田野調查開始著手,這也啟發博傑將地方風土民情轉化為創作,用客觀的方式來看待材料,而非從自身出發,過程中,他也逐漸發現自己特別喜歡用手製作的東西。


喜歡挖掘不同媒材、學習工藝技術的他,有次因為想創作玻璃光學裝置,向相關行業的老師傅請教,起初僅是想多習得一個技能,過程中,發現鑲嵌玻璃的製程有種療癒的魅力,最後完成後的形態也非常吸引人。「其實鑲嵌玻璃很像我的個性。」博傑笑著說,有別於以高溫製作的口吹玻璃,而是利用切割、焊接,這種理性的冷加工,呈現充滿溫暖、療癒人心的氛圍,就如同博傑在率性、風趣的外表下,內心也有十分感性的一面。


逐漸消逝的鑲嵌玻璃技術
說起鑲嵌玻璃的出現,其實是從燈具品牌Tiffany開始,當時他們為了將手工玻璃與珠寶融入燈具,而發明了這個技法。由於過去台灣是代工大國,也曾為歐美國家製作玻璃,經常從國外進口材料,再外銷成品出去,國內也因此帶起壓花玻璃的需求,如海棠花、十字、條紋等常見的壓花玻璃被大量使用,但由於製作昂貴、耗時,隨著時代的發展,這樣的技術需求已逐漸消失,材料也越來越少。

「玻璃的種類非常多,每種都有不同的表情,但我希望一次說好一個故事。」便在品牌成立初期,選擇用台灣人最熟悉的壓花玻璃,以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燈具,作為呈現形式,而後也逐漸增加不同的玻璃種類。品牌取名為真真,字面上來解讀,是用一對雙手作出真摯的物件,但更深入來講,鑲嵌玻璃是很物理性的製造過程,切壞就是切壞、焊接失敗就是失敗,無法拐彎抹角或遮蓋瑕疵,是很真實的。



無法表達的話語 就讓光來延續
現在博傑除了致力於發展鑲嵌玻璃工藝之外,也持續以多媒材的方式做更純粹的創作,他笑說,自己其實也不斷把當代藝術的元素,偷渡進真真這個品牌,從單純的燈具,往更多元的方向發展。「我想做有別於過去,需要了解藝術背景,才能看懂的作品,而是更直觀的欣賞方式。」既然有些感受無法用言語表達,那就試著用作品,以最少的語彙描述,表達深遠的意境。

對他來說,每一項作品、每一片玻璃都是獨特的,也因此,在不同的合作通路,或是當客人訂製時,都會先花些時間了解擺放的空間樣貌、主人個性。博傑說,曾經有客人帶著家裡的老窗花前來,請他做成適合新家空間的燈具,將過往在老家的回憶,以新的方式延續到下一個住處,讓他特別印象深刻,而這也正是博傑想傳遞的:燈具如同光的記憶物件,可以脆弱,也可以很雋永。



抵達於光的前方
這次即將在三徑舉辦的展覽「抵達於光的前方」,除了能夠看到幾乎所有製作過的品項造型之外,還有更多特殊的玻璃材質,無論是色彩搭配、花樣紋理、高溫燒製時產生的意外變化、甚至是玻璃裡的氣泡,都是平日少見的,雖然也許在大量製造的商品裡,這些特殊品可能會被視為瑕疵,但在博傑眼裡,這些都特別迷人。


所有的品項中,以燈飾為最多,從多片不同的造型組合,到單片圓盤都有,還能更換材質,除此之外,也有以銅管串聯燈泡、玻璃的特殊款壁吊燈,跳脫了以往對吊燈的想像;或是將植物放入燈器,使美麗的光影亦有自然的相伴。「我想把過去的工藝,用當代的語言呈現。」博傑說,他也將鑲嵌玻璃製作成精緻置物盒、項鍊耳環飾品等,讓人能透過不同形式,來認識傳統工藝的美。



由於三徑就荒的氛圍較為寧靜、沉穩,博傑認為,若以沉浸式的展覽方式,應該能帶來跟以往展示空間有不一樣的感受,因此期望藉由多盞吊燈不同的光源,打造幽暗的氛圍,讓人在其中慢慢適應,進而感受與發現空間的樣貌。
透過雙手引領與製作,就像在高速超載的現代生活中,就像是博傑讓自己緩衝下來的過程,不再依賴腦袋的既有邏輯,而是藉由開啟身體不同感官,來享受創作的樂趣。去年真真與藝術家許雁婷合作,將黑膠唱針接觸玻璃的紋路,所產生的聲音轉換成音訊後,編曲成專屬品牌的音樂專輯,未來希望用更多不同的面向來完整品牌樣貌,讓玻璃藝術可以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