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的購物車是空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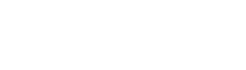

去年夏天,因為一場台南之旅,我們認識了刺繡品牌風花與梅波,兩個品牌雖然同是以繡線為媒材,風格卻截然不同,風花多彩細緻,梅波優雅氣質,進一步深聊之後,才發現兩位創作者--心慈和達達,原本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,因著各自的契機,接觸刺繡這項技藝,勇敢地跳脫既有的生活樣貌,將心中的無限想像化為美麗的飾品。這次邀請兩人來到三徑一同辦展,開展之前,我們也和兩位聊聊關於各自的品牌緣起,以及創作與自身的連結。


問:兩位從上班族轉為經營品牌的契機為何?請和我們分享當時的想法與過程。
慈:成立風花前,我在台中的資訊媒體產業工作,雖然跟刺繡或設計沒有太大關聯,但我從小就很喜歡、也擅長做手工,常常當班上的學藝股長。兩年前因為興趣,開始自學縷空刺繡法,有次到苗栗苑裡藺草編織協會,所舉辦的編織藝術季的擺攤,起初只是好玩,沒想到客人跟主辦單位的反應都非常好,讓我開始思考也許刺繡可以變成我的工作,後來也就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、搬上台北,開始認真做刺繡。
達:我曾經做過行銷公關、居家網站編輯,還有在販賣日本器皿的選物店工作過。一開始做飾品是想自己戴,也曾經嘗試過陶藝和金工,但都不是適合我生活習慣的媒材,有次回去高雄老家,看到我小時候有個小玩具,是把繩子放進去轉一轉,就會變成一條串珠,而家裡也有很多罐小玻璃珠,就想也許可以將它結合線材,就可以帶著走,尤其我又很常在高雄台北往返,若能有可以帶著去旅行的材料,何不試試?




問:兩位雖然皆以繡線為媒材,但風格卻十分不同,請說說自己的作品特色,以及靈感來源。
達:我喜歡在刺繡裡加入弧度,製造一些光跟影,讓飾品跳脫平面。像是我的作品「月半菊」、「柳半菊」,就是由一瓣一瓣的圓弧組成,這靈感來自過去在日本食器選物店工作時,常在碗盤上看到的日本皇室家徽菊紋。有時我也會翻閱登山圖鑑,看看上頭的手繪花朵跟果實,但其實無論是花還是植物,實體永遠都比人做出來的漂亮,所以我也沒有想把花看得很細,就是先看在眼裡,再回去變成輪廓,確定之後就在框框裡自由發揮;有時也不見得是看到什麼,就是先隨意畫,製作時再花時間跟它慢慢相處,才有其他的文案或是想法會逐漸發酵。
慈:我很喜歡幫作品取擬人化的名字,像是花火節縷空刺繡耳環系列的「理惠小姐」、「洋子小姐」,是從還沒有創品牌之前,就在想像如果有天我做這件事,然後客人會跟我說「我今天帶理惠小姐出門」,感覺就會超可愛,名字搭配的色彩則是靠想像,像理惠小姐就讓我想到宮澤理惠,可能滿適合白、藍與卡其的配色;洋子小姐感覺是出國歸來,一位知性的女子,因此使用綠、藍,還有一點白和橘點綴。
我也常在作品當中加入互動性,讓大家看到、觸碰到後有驚喜感,希望看到它的時候,不是只有單純覺得漂亮,還有更深的東西在裡面。像有次去聽一個日本織品創作者的講座時,他分享了一款絲巾作品,平視像是幅畫,拉起其中一角則變成像花束一般,讓人很有驚豔,當時特別喜歡這個概念,後來有次看到自己畫的魚,開始想像若我把尾巴放大,做得像花一樣會怎麼樣,於是就有了「金魚花」這款,讓人因觀看距離不一,而有不同感覺呈現的作品。





問:覺得作品跟自己的個性有什麼樣的關聯呢?
達:我的作品其實跟我個性是相反的,我不太喜歡引人注目,所以以前飾品都買很小、做陶、插花,也都小小的。
慈:對耶我記得你以前跟我說,你不放彩色的東西在身上。
達:後來有次看到日本雜誌《FUDGE》有一個女孩帶著大耳環的畫面,覺得天啊!對比的感覺太強烈了,那個耳環也很大,就自己做了一個,發現原來我也可以駕馭。
慈:我的作品除了直觀的樣貌之外,還有很多細節等待大家發掘,其實也是在反映我自己,希望別人看到我的內在,但若以色彩來說,我的作品跟我也不算是符合的,因為我穿衣服偏單色系,比較少會在身上穿得五顏六色,但是我的作品從一開始就都是滿多色彩的,是我發現自己擅長搭配顏色,常會得到大家的讚美,所以還滿喜歡嘗試不同配色的。






問:說說這次在三徑展覽「無須寶石,也閃閃發亮!」的想法。
達:這次展覽名稱取名為「無須寶石,也閃閃發亮!」是因為我們的作品雖然都不是珠寶,也沒有加入珠寶,但戴起來就像是打了聚光燈一樣,吸引人的目光。
慈:閃閃發亮,對我來說有兩層意思,一個是飾品裡使用很多金屬線或玻璃珠,讓你看起來真的閃閃發亮;另外一個則是讓你戴上去後,整個人散發出身上閃閃發亮的光芒。


問:這次展覽是否有推出新的作品?
慈:這次有幾個有多種帶法的耳環,像是「珊瑚」、「山苦瓜」和「浪」,「浪」的靈感來源是花蓮的海浪,它是由兩個顏色不同、大小不一的圓所組成,大家可以自由調整圓的方向,戴起來會有不一樣的感覺,中間還加了一顆珍珠,代表日出時從海平面出現的太陽,綻放出微涼的光芒;也有從剛剛提到的金魚花概念「遠看以為是__,近看原來是__」所延伸的「是花,還是眼花?」,刻意將蝶翅膀放大,身體縮小,試圖讓人再次產生視覺錯覺(笑)。其他還有像是從過去學習服裝製作時,特別感興趣的抽褶技法所延伸的作品--「抽皺的花與籽」,是將布料換成繡線,抽皺之後就成了一朵朵自由生長的花。這款使用的是我收藏已久,卻一直找不到使用機會的精緻銀白繡線,柔軟光滑的觸感,再點綴幾顆花籽作為點亮收尾。
達:我的話就像剛剛提到,我常會把瞥過一眼,卻印象深刻的畫面變成輪廓,再慢慢描繪,像之前剛好看到雜誌上,有位model站在因新冠肺炎而空無一人的海灘上,後頭一張張收起的白洋傘特別吸引我的注意,便把它繡出來,也期待疫情過去,白洋傘再次敞開的樣子;還有之前去澎湖玩時,看到二崁社區許多戶人家會用海廢裝飾自家庭院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小漁網用的浮球,就把浮球漂浮在海上的樣子描繪出來,成了「沿海之上」。
除此之外,最近我也開始留意一些平時常見,卻鮮少注意細節的植物,像是「藍莓有花」、「含羞草有花」跟「洋甘菊」,其中藍莓跟含羞草都是生活中常出現,但我卻想不出他們的花朵長什麼樣子,查了之後覺得很有趣,就用繡線記錄下來,提醒自己也告訴大家:他們其實會開花!














問:在創作的過程當中,覺得帶給自己的力量是什麼?
慈:我覺得是讓我找到跟自己人生的共鳴。我有一些作品,其實是從失敗品開始的,會說是失敗品,是因為原本我想要做A,但在刺的過程中,它卻變成另一個樣子,雖然對A來說,它是一個失敗品,可是單看它本身,其實還是很有意思的作品,就像在人生當中,有時候遇到很糟糕的狀況,會忍不住懷疑自己,覺得我會繼續慘下去,但只要過一段時間跳脫回去看,你會發現那個糟糕的事情,也許讓你變得更好。
達:我覺得能把一個東西從無到有製作出來,真是太棒了,每當我有些想法,只要身邊有材料就可以實現,直到現在,每次開始繡之前,都還是覺得很興奮、躍躍欲試。雖然因為沒有設計背景,所以開始想要進入設計產業時,會擔心自己是不是沒辦法做到,直到現在,我已經跨過那個恐懼,成立了一個品牌,它帶給我的力量就是think big,勇敢一點。




















撰文/吳亭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