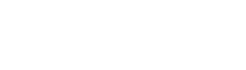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曾在《陰翳禮讚》提到,「東方人擅長無中生有,借陰翳之生,創造了美。美並不存在於物體,而是在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陰翳與明暗之間。」初次看見藝術家林希羽的作品時,心中不自覺想起這段形容,她透過多張不同灰階色調的版畫拼接、膠合、塑形出各種不同紙塑件,在光影的照射之下,散發出寧靜、溫潤的氛圍,周圍的時間彷彿也慢了下來。 希羽的創作之路可以說是從大學開始,雖然過去沒有美術相關背景,但因嚮往設計的世界,便在大學的就讀志願單上,填下所有與其相關的科系,最終在建築領域中,遇見創作的更多可能,也讓她從此有了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。 恰好當時因台灣建築法剛推出了「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,用以美化建築物與環境」的規定,使得公共藝術蓬勃發展。畢業之後,她便跟著老師接相關案子,參與像是地景藝術節或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布置,不過對希羽來說,這樣的作品與其說是「藝術」,不如說是透過「設計」來解決場地與雇主提出的需求,創作者本身的個性並不明顯。 「在建築系裡,要知道什麼自然環境適合怎樣的材料,建築物裡、外適合的材質也都各有不同,會接觸到非常多種材料,因此對於材料的包容度非常大。」希羽說,也許是在這樣的教育訓練下,讓她習慣嘗試各種媒材,從不侷限自己,但反過來說,她也並沒有最擅長、最能表達自己的方式,這個想法在她到芬蘭藝術駐村時體悟最深。 [2015 芬蘭 約察] Haihatus International 4 聯展作品 作品 / Light stitcher媒材 / 胚布, 咖啡染料, 聚脂纖維棉, 燈具 作品 / Light stitcher媒材 / 胚布, 咖啡染料, 聚脂纖維棉, 燈具 [2015 芬蘭 約察] Haihatus International 4作品 / 林圖 Birds媒材 / 胚布, 咖啡染料, 聚脂纖維棉, 素描紙, 鉛筆 尺寸 / 布雕塑 高度 35 cm, 素描 40x60 cm 「那次的駐村經驗對我來說衝擊滿大的,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如何創作、生活、怎麼透過作品表達自己想說的話,也讓我開始回頭思考自己的創作。」她發現自己過去的作品,大多是針對空間、業主需求回答問題,鮮少思考從自身出發,主動表達自己想傳達的。回到台灣後,她曾試圖複製芬蘭的駐村經驗,和朋友在台南成立「實驗厝」、到台東做駐校藝術家,而美柔汀技法就是希羽在這段期間認識的創作方式,也是開啟她投入版畫與紙媒材創作的契機。 美柔汀技法是一種版畫的磨刻技術,不同於傳統大家較熟悉,需要使用藥劑的腐蝕技法,而是利用刮刀跟壓磨刀在版上,建構出不同程度的粗糙面,它能調整上色時的油墨附著度,呈現不同層次的灰階,其幽暗、朦朧、似是而非的狀態,特別讓希羽著迷。 美柔汀銅版畫/mist forest 1-7, 2020 系列作品 / mist forest-1, 2020媒材 / 銅版畫,義大利版畫紙,燒綠青水干顏料 尺寸 / 銅版畫 14x14 cm,紙框 19.5x19.5 cm 作品 / mist forest-4, 2020媒材 / 銅版畫,義大利版畫紙,燒綠青水干顏料 尺寸 / 銅版畫 14x14 cm,紙框 19.5x19.5 cm ...